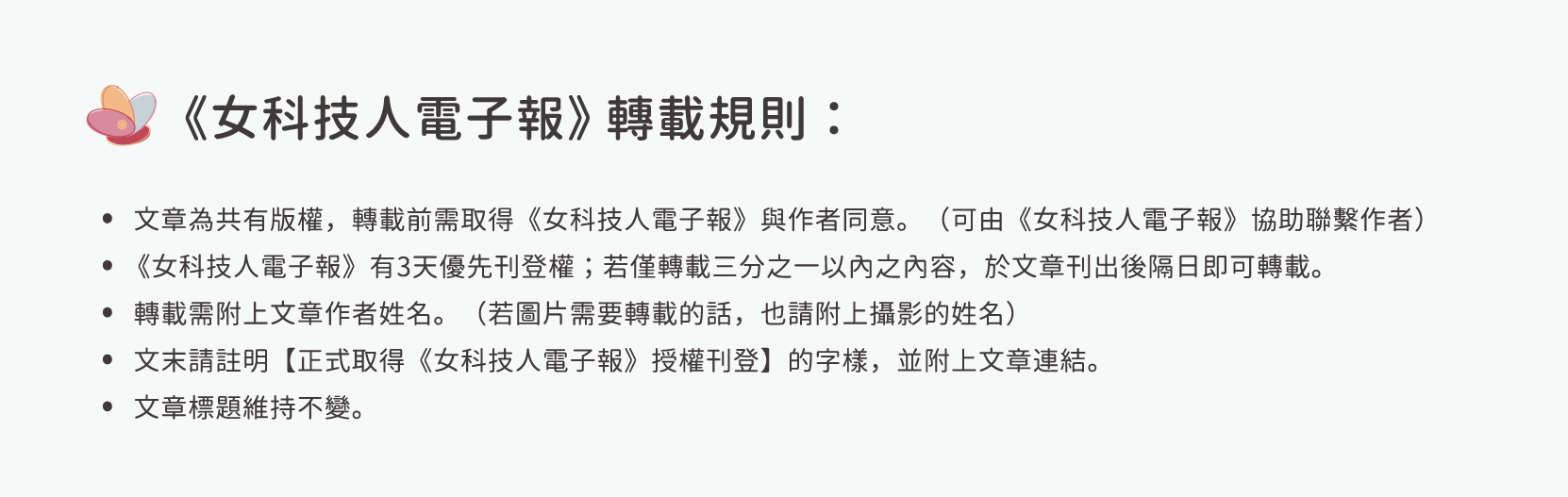看完宋郁玲教授在《台灣女科技人電子報》2020.07.14第151期發表的一文,讓我有感而發。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不想再繼續用「微怒優雅」的語氣呈現那個年輕時受盡委屈的自我。「老師,妳為什麼不直接的表達?」有一位被我指導的女博士如是說。是的,「我為什麼不說,我有什麼害怕的?」這是我常問自己的話。還有「如果我不說也不寫,誰會寫?」十年之前退休離開原來的研究室,從四樓搬到六樓,讓我看到了藍天與小山丘,可以盡情的想像我該是一個怎樣的人,如何能把學者的角色扮演得更好。
在地理學界這麼多年,我有過很多體驗,可以拿出來與讀者分享。我提出的例子,可以來自婚姻中的性別角色與就業,空間尺度可小可大,從個人的感知到全球現象,也可以從科學的觀點、理論的角度切入討論。其實性別議題絕不是婆婆媽媽的事。多年以前,我參加了一次國是會議,一篇有關家暴的論文交到一位男性人類學者手上,要他講評。他把文章拿起來再放下,有關文章的內容什麼都沒說,卻直截了當地回應:「這篇文章為何在國是會議上發表?」看到 A 君(化名)如此地無理,讓我對他大為失望,據說他從人文地理轉念美國某名校的人類學系,他太太剛好是被我教過的,告訴我A君為了把博士念得好一點而延畢。那天除了當場傻眼,記得主持人也沒有對他的大放厥詞做反應,席間也沒有人發言抗議。這篇文章就變成沒有人評論了。如果一位70年代在美國花了一段時間念博士的人,對女性主義人類學無感,那是多麼的不可思議。幸好臺灣大學在聯合國婦女十年的最後一年成立了婦女研究室,雖然當時沒有從美國拿到女性主義相關學科的學位,許多學術界的婦女已經覺醒,臺灣的《婦女新知》雜誌社已經在1982年成立,臺灣知識婦女已經冒出來(awakened),只是還未站穩腳步,但並不是置身事外。
1984年,作者因為寫了臺灣城鄉婦女遷移的博士論文,而被邀請到英國 Durham 開會,認識了一批女性主義地理學者,來自好幾個國家,也因為該會議是由聯邦地理局(Commonwealth Geographical Bureau)所召開,與會者只有英聯邦國家的才得到旅費的補助。
我自己雖然沒有開過女性主義地理學為名的課,卻努力不懈地出書《性別、社會與空間讀本》(2016年),在研究中注入性別觀點,而且在屏東科技大學教過兩性關係這門課,也把性別角色放進所有教過的地理課程中。雖然課名可能一再重複,教材卻是每年在更新的。退休以前所提過的研究計畫也不例外的涵蓋性別視角(feminist perspective)。
退休之後,還是一直以性別視角做研究。如今婦女與性別研究已經不需要學術界的肯定,研究的成果,在國外的期刊經常可見,而科技部(前國科會)在申請研究計畫時,只要在申請表上加上代號H24,就能夠辨識學科別。說真的,前人的努力,加上新一代學者的接棒以及影響力,大家可以看到這三十五年在研究及學科上的成果。
宋教授所言,女博士在學術領域中的步履艱辛,卻真有其事。回想筆者1972年初到臺灣時,花了四個月的時間才拿到身分證之前,幸好完成了一本113頁的碩士論文,而在半年之內獲得兩份兼差的教職,一是在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教計量地理,二是在臺大教大一英文。真要感謝當時的兩個系主任多麼的開明,任用一位國語講得不夠好的香港年輕學者,而筆者對於當時一共拿到新臺幣1,440元的薪酬也如同嚐到甘露一般的感謝。因為由此開始有學生教,就有人可以說話,好像在一個陌生的地方找到一扇沒有鎖的門,一窺內幕。人生地不熟的我就這樣進入學術圈了。學術像是我在沙漠中找到的綠洲,我死也不肯離開她。
宋博士指出,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在2017年針對全臺41,919位博士進行抽樣,有5,243位博士接受了問卷調查,其中女性比例從2004年的 25.6% 上升到33.1%(NPHRST 2018)。而因為當前社會普遍認為女性為主要家務承擔者的狀況下,導致女博士在學術領域中步履艱辛,已婚女博士仍然承受著更多的生存壓力。
由於學歷上的要求,拿博士已成為進入大學任教的第一道門檻。臺大地理環境資源學系的女博士逐漸增加。一般來講,升等方面還算好,只是歷年來擔任教授兼系主任只有兩位女性,而其他的大部分男性卻是一帆風順的升等、拿國科會研究計畫、獲得特聘教授、當系主任或是在臺大兼其他行政職,也大部分結婚生子。表面上,系上看不出有太大的性別議題,會對自己人生及事業造成衝擊。學術工作畢竟對一個母親來說,可賦予較大彈性,沒有上下班時間的壓力,也沒有非升等不可的壓力,甚至有輪流當系主任的假設,也沒有硬性規定的用在女性同仁身上。
學而優則仕的情形很明顯發生在男性同事身上。目前中國地理學會的理事當中,女性占四分之一,理事長一職,目前只有過一次由女性擔任。女性擔任理學院副院長的有過兩次(姜蘭虹、周素卿),多年以來理學院也只有過一次由女性擔任院長,跟著她被聘為中研院副院長。目前臺大只有一位女性副校長。作者認為,可能是與臺大有重理工、輕人文的關係有關,傾向於理工專業當上院長的機會,男的較女的多。
筆者遇到人生的第一個難題就是身為女的大學教師這件事,因為性別而帶來的刻板印象一直存在。1970年初期來臺的筆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想這四十多年以來,筆者並不是一個一開始就是一個女性主義研究學者,只是在家庭角色上扮演上感到比在事業上要挑戰很多,隨便回想一下就感到自己在家中受過不少「委屈」(如宋教授之文中所述)。我從小生長在姊弟和自己之間相對平權的知識分子家庭中,一下子到了臺灣「性別化」(gendered)的家庭,很難適應夫家長輩的要求,本能地排斥。縱使我的舉止「優雅」(ladylike),卻無法順著半世紀前的臺灣社會價值,對職業女性的要求、協定(protocol),及許多限制下度過人生。大致上有五方面,我違背了傳統女性要扮演的角色:
- 我從一開始當講師就很投入事業,除了教課以外,亦參與各種公共場所的學術活動。1994年我當系主任時,積極籌備了第四屆亞洲都市化會議(Fourth Asian Urbanization Conference),安排會外考察北中南三個市,參觀當地的都市及工業建設。
- 我就業的第三年出國參加學術會議,第四年到夏威夷大學念博士。
- 我沒有照婆婆的建議服侍先生,也沒有犧牲自己的事業,全心全意照顧家人。
- 身為父母都是知識分子的女兒,我壓根沒想過自己扮演相夫教子角色的樣子,像是辭掉工作、要比小孩及先生早一步回家、偶爾還要對夫家長輩請安等等。
- 在先生的家族中,我恐怕是第一個上桌與其他男性一起吃飯的媳婦,也可能是第一個在客家庄溪邊釣魚的女人。
來臺的頭三年,也是人生最煎熬的一段時間。我無法忍受臺灣父權興盛的家庭文化而毅然決定暫時「拋家棄子」,出國到夏威夷大學再念博士,也花了一段時間,才找回自我價值,不怕再與批評及指責我的長輩互動。藉著充實及知識訓練出無比的毅力,終於擁有獨立的人格,我也勇於在夏大嘗試多元文化的環境,不畏艱難越過求學時代的關卡。由於我個性溫柔善良,獲得很多異國友誼,也認識了幾位已經當母親的亞洲女性出國求學位。當然,我也承受著不輕的罪惡感,以及心酸的求學過程,家人的支持即便需要,更要有自己的決心與堅持
直到1982年,夏大地理系才出現第一位女教授Nancy Lewis。有幾位男老師不太了解為何女人要讀博士,有一位論文委員很直接的告訴我:「以後不會再收一位像妳們這些離開家庭到國外念博士的女人。」他說的另外一位是來自孟加拉國的Rosie Ahsan。她的家人一直催她的指導教授給她博士論文口試,讓她早點回家團圓。
我住的臺大宿舍只有一位楊懋春教授在等交通車時對我說過一些鼓勵的話,「我知道妳出國讀博士很不容易,妳會成功的。」後來我才知道他是當時農推系的教授,是20世紀中國學術界極有成就的鄉村社會學家,曾著有A Chinese Village: Taitou, Shantung,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他一生堅守學術及教育崗位,作育英才無數。
當時我在選博士論文題目時,也是因為我要研究城鄉遷移婦女,受到幾位委員的質疑。一九七零年代只有看到報章雜誌披露此現象,而幾位男性的社會學者(如Parish、Speare及Huang)都對女性遷移者隻字不提,在題目上不說他們採訪的全是男性。1976年筆者從地理系王秋原主任那裡得到福特基金會補助的通告後,申請到一筆可觀的研究經費,正好用在田野調查、資料分析及請了一位得力助手,由地理系學生協助展開農村調查,共訪問八百戶以上,也繼續追蹤移到臺北縣市的女性將近一百人,寫成一本像樣的論文,對升等很有幫助。
1985年在臺大人口研究中心成立婦女研究室,是另一項意外收穫。當時臺灣亞洲協會補助學者及實務工作者出國開會,辦工作坊及國際研討會,為之創舉。由於投入婦女研究室工作的頭四年,筆者認識了一些同行的學者及機構,參與國際學術會議及合作研究的同時也感覺到之後臺灣婦女研究進展得很快,成立研究室的進度、開課的頻率都令其他亞洲國家刮目相看。三十五年以來投入的學者在出版上可圈可點,原先保守又封閉的社會已經無法用父權的價值架構來決定知識女性的命運。女性若懂得愛惜自己及善用資源,在變遷快速的大環境可以找到發展的利基,不要因為別人的責備而感傷及氣餒。世界在變、在創新,好多加諸女性的價值觀已經落伍了。作為婦女與性別研究的先行者,也不要自滿或驕傲。我們歡迎大家加入我們的行列,再接再厲把追求兩性一樣被尊重及平等的目標一直傳下去。
美國的婦女地位,雖然離開與男性平等的狀態還有一段路,可是看到幾個傳統上由男性從事的行業都已有所突破,例如醫科的女性及工程學的女性有明顯的提高。
和我相關的職涯,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就是筆者於1990年被選為Elizabeth Luce Moore Fellow到香港中文大學地理系訪問一整年。雖然同事清一色都是男性,他們的談吐令我感到自在,不會像剛到臺灣時老是被問「妳先生在忙什麼?」或是「妳不在家時誰在看小孩?」倒是有好幾位同事偶爾告訴大家,「我要去接小孩」或是「今天下午我要帶小孩去看醫生」。這點很像現在臺大地理環境資源學系上年輕男同事常做的事,也不怕同事知道。
優渥的獎助對我的學術生涯提供了實質的自我培訓機會及功能。我由香港中文大學同事那裡知道了幾位與他們互訪及學術交流的中國學者,包括了廣州中山大學的許學強副校長、河南鄭州大學的林富瑞教授、昆明大學人口所的陳旭光所長,以及北京大學的曾毅教授。除此之外,我也得以趁著課餘時間跑了好個亞洲國家,包括印尼、印度、孟加拉、泰國、日本與韓國。這種增廣見聞的機會讓我培養了獨自考察的自信,而學到使用學術網絡的技巧,例如我一口氣訪問了南亞幾個城市,是靠著以前的同學與素未謀面的學者。這個獎學金每年只會給一位亞洲女性學者,由活躍於國際女青年會的教育家、慈善家及志工Elizabeth Luce Moore(1903-2002)發起;她曾擔任Luce Foundation 董事六十三年之久,她的父親為美國的報業鉅子Henry Luce(1898-1967)。
地理學培養的人才在跨領域方面很寬廣,也值得很多學科參考。只要我們不要自我設限,不受專制或偏頗的意見相左,我們的學術細胞可以不斷的分裂,產生影響力。如果看遠一點,選對了方向,鍥而不捨地把事情做好,往往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我在念博士時遇到出難題的老師,讓我找到具時代意義的題目,也在國際上人口遷移學門嶄露頭角。好在我因為無法忍受臺灣 70 年代父權家庭的壓迫,讓我暫離家庭去尋找自我,而走上了婦女研究之路。我相信女科技人們一定都有精彩的故事和大家分享。我希望這篇短文會引起一些共鳴,就如同我把宋郁玲教授寫的短文一直保留到現在,到今天才有感而發,欲罷不能。
社會上對女性角色的期待不會馬上改變,除非我們敢去實行。妳可能要有兩個條件:一是妳對工作有超乎常人的熱情,二是妳有兼顧家庭角色的本事,如果在家務上找到分擔的人,就會很不一樣。記得吳健雄女士她的女學生說過:「不要因為妳要付高的薪水給幫傭或褓姆,而不請他們幫忙。」臺大地理系有一位男教授的太太,也是畢業於臺大的,聽說她上了一天的班,先生就開始抱怨了。她的先生說:「妳如果無法兼顧家庭,就不要外出工作,我的薪水可以養活一家五口,妳如果去上班,小孩誰看?」這種故事到現在還是會在臺灣中產階級社會上演著。
過去有一些研究家事分工的論文,我們絕對不能把這件事當作「婆婆媽媽」的議題,而是可以投稿到各類雜誌刊登,絕不止於婦女雜誌。我觀察到,住在我們舟山路「博士村」的男教授,大部分的太太在婚後放棄工作,而最近的二十餘年,我看到先生們拿著垃圾及廚餘去倒掉,會做資源回收,會買菜或便當回家。在五十年之前的臺北市是難以看到的。走筆至此,我不禁想起我每次出國開會,總會有一兩個鄰居太太追著我問:「妳出國時,小孩誰看?」而那時在夏大進修的幾位陪讀太太,也會對我「單身赴學」讀博士,感到很好奇。一到假期就有人追著我問:「妳為什麼還不回臺灣?」我早就該領「最佳勇氣獎」,因為我確實突破臺灣傳統女性的角色,而今天可以全盤托出。
雖然筆者不是典型的女科技人,但是在臺大理學院的地理環境資源學系至今待了四十八年,而之前在香港大學畢業於地理與地質學系,也教過自然地理及計量地理。由於在臺大地理系對性別議題有過長期的觀察,也投入婦女與性別研究,女性主義地理學研究三十五年之久,我已經成為女性主義地理學者(feminist geographer)中的先行者。
身為香港女性,在大學階段求學時,筆者不曾經歷過明顯的性別歧視,反而見到班上的女同學比男性更專心於學業,成績較好,畢業後也有很好的出路,在社會上嶄露頭角。等到結婚後來臺灣,筆者才面臨許多不可思議的被對待方式,筆者在工作發展上還算順利,但確實遇過《女科技人的理性與感性》一書所指的「家庭與工作」的拉鋸。如果主編允許我把自己的故事也加上去的話,可以放在「不屈服的女性學者」專題下。
筆者還記得早期討論職業婦女時,女性常常被問「在婚姻與事業間,妳要選擇哪一個?」我當時的反應是「為什麼這個問題只問女的,而不問男的?為什麼我只能選其中一個?」而如今我已身經百戰、走出陰影,也走出一條自己的路時,如果有人問我,「如果妳從頭再來,妳還是會走同樣的路嗎?」我會回答說:「會的,因為我做了對的選擇,沒有放棄家庭,也無需放棄事業。」家庭與事業不是魚與熊掌,那是一個虛構的比喻,我認為只要女性在兩方面都用心,用對了策略,就可以兼得。現代的女性學者若要成功結合她們家庭與工作的雙重角色是沒有問題的。我認為現代女性走的路會愈來越寬廣,受了高等教育的女性,不用自我設限,應以學以致用來回饋社會。養兒育女,家務勞動是夫妻共同的責任,要不斷協商與調整。我想對大學裡的女學生說:「Girls, be courageous」,如同日本北海道札幌農學校(今北海道大學)的首任副校長 William Smith Clark(1826-1886)當年對全校的男生所說「Boys, be ambitious」一般,年輕女性不用害怕做不到,而是勇敢活出自己。我們看到臺灣這四十多年的變遷,一直都有增加「女性友善」的一面,臺灣社會過去傳統的性別角色都已經鬆動,未來的十年,女性可以積極的、有創意的參與社會,比我這一代的職業婦女活得更加自由、平等與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