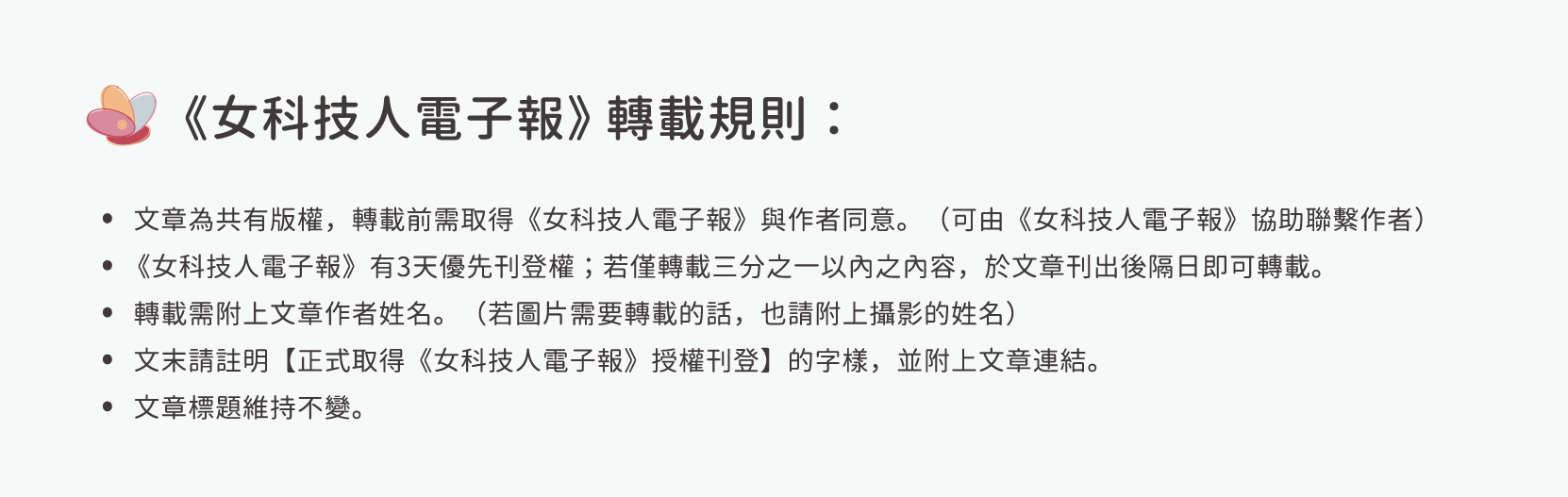《實驗室生活》(Laboratory Life)是法國科學與社會學者拉圖(Bruno Latour),早期的成名作。拉圖以人類學家的身份,進入科學家吉耶曼(Roger Guillemin)在美國加州沙克研究所(Salk Institute)的科學實驗室,進行人類學研究。拉圖與伍爾加(Steve Woolgar)於1979年出版一年之後出版詳細描述科學事實的社會建構專書,實驗室的主持人吉耶曼,則於1977年獲頒諾貝爾生醫獎,是真正的「雙贏」。
在我的研究生涯中,也曾經有過長達九年的「實驗室生活」,這段在實驗室裡動手做實驗、長期參與觀察的生活,對我後來的學術研究與社會服務,都有重大影響。不過當年我進實驗室,不是為了作人類學研究,讓我進去參與觀察的,也不是什麼諾貝爾等級的科學家。因為各種因緣際會,從1995年到2004年,我在先生鄭尊仁的分子生物學實驗室裡進進出出。
1995年的春天,尊仁在美國完成內科與職業醫學的臨床訓練,並且取得博士學位,返台在台大公衛學院任教。而我則在1995年的暑假,才終於收拾好家當,帶著兩個半大不小的兒女,回台灣定居。到秋天的時候,我們的新家與小孩的新學校就緒了,閒來無事(我在美國「全職媽媽」的生活,除了熱心參與兒女學校的家長會,週末也任教中文學校,其實是很忙的),看完幾本先生書架上的分子生物學科普書,對DNA科學大感興趣,從1995年11月開始,幫他建立實驗室,並且當他免費的兼任研究助理。我從萃取DNA開始,一步一步學做PCR(聚合酶連鎖反應)。
我知道許多實驗室科學家都是夫妻檔,我對分子生物學有濃厚興趣,至今都覺得萃取出「自己的DNA」是人生最美好的經驗之一。不過我實在不是手巧的實驗室科學家,接連幾次PCR實驗做不出來,實在氣不過,請尊仁跟我並肩一起做,電泳他清清楚楚兩條線,我就是跑不出來,臉上三條線。
還好尊仁很快建立好實驗室,也收到好學生,有能幹的研究助理。隔年夏天我親愛的媽媽病了,我在台大醫院進進出出一整年,一邊準備投考台大公衛學院的「健康行為研究所」(當時還只是衛政所的一個組)。我清楚知道,我或許不是很好的實驗室科學家,但可以是很好的行為科學家。1998年的夏天,媽媽等不及我博士班放榜就走了,秋天裡我一身黑衣,成為台大公衛學院的博士班研究生。
進入博士班之後,我雖然不再做實驗,還是常在先生的實驗室進出(當年他的實驗室與辦公室相連)。我無法「隨遇而安」,無法在圖書館或是咖啡廳,人來人往的地方安靜唸書或是寫作業。我需要一張桌子,一台電腦(當年筆電還很貴,也很重),感謝先生慷慨在他又小又擠的辦公室,硬是擠出一個小角落,讓我可以專心讀論文、寫作業。先生的研究生稱我為「師母」,也是我的研究所上課的好同學。博士班六年,我與台大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的師生亦師亦友,其中最大的收穫,就是一路跟隨RCA(美國無線電公司)案的研究。
位在桃園的RCA廠,關廠後爆發嚴重的地下水有機溶劑污染,1998年宣告整治失敗,離職員工懷疑罹癌與地下水污染有關,組成自救會。台大職衛所的師生,在王榮德教授的帶領下,執行環保署的委託計畫,在RCA廠的周遭進行毒理學、健康風險評估與環境流行病學研究。1998年夏天的第一次場勘,我已經考取台大公衛學院的博士班了,但是學校還沒有開學。我剛看完當年美國報導文學暢銷書《法網邊緣》(Civil Action),決定效法報導文學家,跟隨調查地下水污染的科學家與律師,進入污染場址與法庭。地下水污染的調查研究曠日廢時,毒物侵權訴訟要等研究結果發表,才有證明因果關係的證據。在我就讀博士班期間,台大公衛學院的研究團隊發表健康風險評估、毒理學與環境流行病學,三篇研究報告,證實居民健康與地下水污染有相關。而勞委會勞工安全研究所的團隊,勞工職業流行病學的研究報告,則發現曾經在RCA工作的勞工,罹癌的比例較高,但是在統計上並未達到顯著。職業流行病學的研究結果發表後,引發準備提起訴訟的勞工不滿。於是2003年,在我取得博士學位的前夕,國民健康局又委託台大公衛學院的團隊,想要進一步瞭解RCA勞工的訴求。我放下寫到一半的博士論文,帶一名能幹的助理,開始訪談RCA勞工,自救會幹部,以及工傷協會的重要成員。計畫結束後,王榮德教授的研究團隊,重起職業流行病學研究,並且連結RCA勞工的子代,進行生殖危害研究。我在計畫結束之後,順利取得博士學位,並且留在台大公衛學院,擔任專案計畫研究員,協助執行國民健康局的委託計畫。
在台大公衛學院的博士班期間,我已經熟習生物統計與流行病學,再加上參與女學會與科技與社會(STS)研究社群,得到許多女性主義的養分。博士後為了報名參加性別與醫療研討會,我重新閱讀女性主義科學家珊卓·哈定(Sandra Harding)的演講稿「誰的科學?誰的知識?」再次翻閱RCA案已經發表在國際學術期刊的生物醫學論文,彷彿被雷打到。我只花幾天的時間,很快寫完〈女人與水:由性別觀點分析RCA健康相關研究〉,批判討論公共衛生研究裡的性別盲點。這篇論文在性別與醫療研討會中得到許多性別研究前輩的鼓勵,後來正式發表在《女學學誌》。
〈女人與水〉是我所有論文中,「點閱率」最高的。常有朋友問我,這些分析資料是怎麼來的?我的回答都是:「這是我在台大公衛學院裡,超過六年的田野研究。」從1998年第一次進入RCA場址,這幾篇研究報告的討論與計畫審查,我都在場。從完全不懂統計與流行病學,到必修學分終於修滿,懂得其中的眉眉角角,再加上2003年的深度訪談,我清楚知道這些生物統計資料的各種缺失,我知道我的批判討論是有力道的。雖然〈女人與水〉在RCA訴訟初期,幫不了大忙,但是2008年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成立,我開始有正式的教職,又有科技與社會社群的支持,我加入RCA訴訟顧問團,全力協助訴訟。而當年一起執行RCA研究計畫的毒理學家、流行病學家、暴露評估專家則逐一站上證人台,出庭為RCA勞工作證,並且協助反駁RCA公司以高薪越洋請來的專家證人,RCA案的原告勞工接連勝訴。在死亡與罹癌勞工因果關係確立,三審定讞之後,在法庭裡兩造爭執的是沒有外顯疾病的勞工,是否有DNA損傷。出庭作證的,是當年教我做實驗的分子生物學家,我的好伴侶。我坐在法院旁聽席裡,聽尊仁跟法官詳細說明DNA科學,心中有無比的感動。
這是一段神奇的實驗室生活,雖然我的「報導文學」因為RCA訴訟還沒有結束,部分內容還無法解密,但是這個故事的結局,不是科學家得到諾貝爾獎(像拉圖《實驗室生活》的科學家),也不是律師破產(像《法網邊緣》的原告律師),而是一群學者專家、律師與勞工團體一起努力,終於為受害勞工爭取到公平與正義。從我踏入實驗室的那一天擔任免費兼任助理的那一天,這一路以來,真是超級有意義!